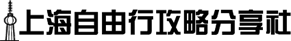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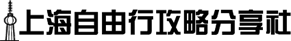
前些日子,107岁高龄的邵逸夫先生辞世,举世哀惋,我亦神伤。一者善人一个,值得大家记念。二者早些年笔者有幸与之曾有一面之缘。更为紧要的是他与我父亲几为同龄。邵老先生和周有光等老伯的皱褶里,还承载着一些他们那一代人的生命与精神特质。在他们的身上,还能依稀看到我父亲的一些影子,拜其所赐,我父亲的生命似乎也因之得以延长。如此岂能不予珍视并深为惋惜呢?
其实,我父亲只是那个时代中国乡村当中最最平凡普通的一介农夫,便似那个年代的一块小疙瘩,但在我心里头,父亲就似横亘于我面前的一座山峰,一道脊梁,迄今让我怀想,让我眺望……
晚清时候,国家积贫积弱,大厦将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秋冬,光绪帝与慈禧相继大薨,年仅三岁的溥仪登基,是为宣统。是年的腊月十六,在失势的袁世凯被籍口开缺,启程回乡养疴之日,正是我的父亲降临人世,开启生命旅程之时。
父亲行四,上面已有一个姐姐,二个哥哥,长我几近百岁的祖父文吉公,当时该已年近半百了(生于1865年)。父亲告我,早年祖父在镇上开有铁铺,可能因是身体有恙,后来回了村里定居。现在的老屋该就是祖父当年所造。月潜光辉,日翳浮云。就在父亲出生二十一个月光景,亦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十月,祖父故去,从此家道中落。好在族中先贤宝时公当年任职上海道台、江苏按察使之际,热衷公益,慷慨捐输良田二千余亩,于故乡芝英设立“义庄”。但凡应氏族裔,家有天灾人祸,如丧夫后携幼寡居者,孤儿寡母可于每月廿,去义庄领取稻谷,糊口维生。按例,每年的三月廿验证,大人每月16斤(旧制廿两,下同)、孩童8斤。小孩长到16岁不再领取,20岁,其母亦被取消,意谓儿子可以也应该奉养母亲了。基于此,芝英应氏人家寡妇改嫁的很少,是以有俗语云:“芝英驮(大),寡妇多。”在那个年代,活着是第一位的。吃义庄谷长大的父亲每当谈及这些,总是深情满满,或者说他的一生充满了感恩之情。我相信这与其良善、纯朴一生的品性养成不无关联。
我忘了询问父亲小时候有没有扎过辫子,其实问了也是白问。因为这个年仅三、四岁的大清遗民一定还未能记事。对于稍长上私塾发蒙读书,父亲的记忆则是清晰的。私塾以每年的端午为界,分为上下两个学期。学费每半年一块银元。每年上半年先生去学生家中集取麦子,抵当学费,同时赠与学生每人一把折扇。平常先生自己蒸煮米饭,菜肴则由学生家庭轮流烧好带来。私塾设于村中应氏宗祠的上房,书桌和櫈子均用厚厚长长的木板制成,一张桌櫈得坐好几位童生。一早起来“抢早学”,吃罢早饭再回祠堂诵读。一开始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而后是《幼学琼林》、《论语》、《先进》、《大学》、《中庸》、《离娄》等等。父亲告我,他七、八岁上学,第一位塾师叫成庐(音)先生,方岩坟头山人。一日先生有事离开,一群顽劣学童立马玩起了蒙眼摸象的游戏。不意先生突然回转课堂,错被眼眶蒙布的同学一把抱住不放,令人哭笑不得。结果该学童不光是“吃红糕”(戒尺打手掌),更被罚跪思过。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每当回溯起这些,布满沟壑的脸上总是划过一丝丝的纯真与笑意,仿佛回到童年。
木刻本《孟子》
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应该只念了几年的四书五经,便不得不辍学了。但正是这难得的几年,开启了父亲的知识与文化之窗。从此喜欢看书、抄书便如同劳作一样伴随了父亲的一生。当我年幼,夜阑时分,万籁俱静。昏暗的煤油灯底下,老父戴着老花眼镜,手展黄卷嗫嚅读书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父亲懂得天干地支六十甲子历史纪年方法和二十四节气的演算与变化。他还喜好音律,长箫、唢呐、二胡样样俱能,曾与村中族人组建“罗汉班”,于农闲和逢年过节吹拉弹唱,陶冶性情,娱乐乡里。父亲通晓《三国》、《残唐五代》、《岳传》、《粉妆楼》等等历史演义故事,对故里以及族中的历史掌故、轶事亦是耳熟能详。每当夏夜纳凉或雪天围炉取暖,他便同我一则则徐徐道来:什么“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薛仁贵征东与寒窑认妻”;“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李存孝打虎”;“芝英应贻诰,做官做倒灶”等等,每每将我引向一个个久远、神秘、传奇的世界。待我长到五岁之际,父亲便急不可耐教我手执毛笔写字,更把每年自家及邻里托写春联的事交付于我。父亲生性纯良,待人和善,尤与识文断字、喜好文史者投合、话多。他时相聚晤、往还的好友除了本村的同好者外,还有湖田村的双佑先生、岭脚村的岩星老伯以及孤清自守,索居灵岩福善禅寺的圆松法师。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记忆中这位年逾九秩的大师,六岁出家,道行高深,唯不戒酒肉,鹤发童颜,望之肃然。
手抄戏曲唱本《姜维探营》
父亲偶或也有浪漫新潮之举。其最后一次的徒步远足行旅该是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已负笈杭城,这是姐姐事后告诉我的。那一年的秋日,风清云淡,柿黄菊白,满山红叶。父亲肩挎盛满棕子、麦饼之类干粮的布囊,携手同样也是满头霜雪的母亲外出云游。先是循着独松、桐坑方向,一路爬山涉水,游观沿途景致。期间到过缙云的张山寨,拜谒学法成仙后,拯救苦难民众、助人圆梦而被后人建庙供奉的陈十四娘娘。尔后转道去往位于永康、磐安、缙云三县交界处的仙师殿。最后到了同样位处深山的岩星老伯家小住。“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想必唐朝诗人孟浩然描写的正是这般情境。父亲与岩星老先生结缘、相交多年,友情诚挚。父亲曾经告我,他年轻之时有一次做客于此,适逢夜里有土匪前来袭扰。父亲与岩星家一帮壮丁持火铳据高苦守,逼退匪徒。这一次当属父亲的告别之旅。酒逢知己千怀少。庭院里、夕阳下二位老人把话当年,滔然不息,都喝了不少自家酿造、密封存放多年的老黄酒。这也是俩位老人的最后一次聚晤,便似回光返照与最后亮相。因为不出几年,俩位老人的生命之舟便都相继倾覆、塌陷了。
父亲虽然好学,却终究没有读书的命。其时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唯一的姑妈已做了人家的童养媳(据言这位既是亲戚又是日后的婆婆对姑妈十分的刁钻刻薄,兴许童养媳的命运大抵如此吧)。那个年代争战频仍,饿殍饥荒,病疫恣肆,而又缺医少药,父亲的二哥便在9岁的时候夭折了。我生长于斯的村庄,早岁有几样谋生的行当,一者割蒙芯。这是一种生产蜡烛的材料,收割打捆后运销到德清的新市。二是开设冶坊,铸造铁锅。迫于生计,父亲缀学了。第一次出远门,随族中长辈去往处州采割蒙芯。割蒙芯都在深秋隆冬季节,寒风凛冽,冰水刺骨。我依稀的见得霜天雪地之间,一个14岁的稚嫩少年艰难地跋涉于溪滩两岸,衣着单薄,手掌皲裂的样子……。
绘本《粉粧楼》
父亲告诉我,1926年出外谋生,时在常山,适逢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浙境,队伍整齐,纪律严明。军队雇用挑夫,从常山去往衢州,八十里地,给白洋两块。再后来,父亲去过龙泉的八都、安吉的孝丰、递浦等地的冶坊,做学徒、当师傅、搞销售。有一年在八都的时候,得患疟疾,病情延沓。父亲怀乡思归,独自一人,踽踽跋涉,病笃途险。,,不少省级机构亦散落于其周边一带,当中便有医疗机构设立于世雅边上的王家村。父亲去配过好几次的药,总算转危为安。否则也便不会有今天的我在此述写为文。呜呼!个体生命诞生与存续总是有太多的偶然!
父亲年轻时候曾被抓壮丁,因此穿过几个月的军装。其时我大伯父亦已亡故,家中只有我父亲一个男丁,按理二抽一,轮不上我父亲的。那是1938年的闰七月,我父亲连同镇上其他的壮丁,被用绳子捆扎连串在一起,押解到县城的徐震二公祠关押、操练。可怜产后仅半月余的我母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求人,递状子。更迈着小脚几度步行三十多里地赶往县城探视。最后,在父亲即将被送往战场前线的前一周,终于“讨”回了自己的男人。其时我大姐已经二岁,大哥则刚刚出生数月。可以想见,一旦父亲去往前线,当了炮灰,这一家子岂不又悲剧重演了吗?谈起往事,父亲平静安然。
工尺谱
兴许当年的纠结与沟沟壑壑早已被岁月掩埋磨平。父亲的一生,物质生活并不富有甚至是艰困的,但我深知并确信一点:他的精神世界一辈子都是宁静、丰裕和敞亮与温暖的。这从他一生厚德温仁、乐善好施可以得到佐证。父亲告诉我,四九年前,他几度被荐举担任保长,幸好都被他“英明”地加以婉拒辞谢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倒是新政之后,兴许是出于朴素的感情,在乡亲的推举下,他曾在农协、合作社里担任过一些职务。只是我想,在讲求斗争哲学的年代,我父亲的品性与时势似乎并不契合。事实上,。
小时候,父亲不止一次给我讲过一个《十金贤名》的故事:从前,有个书生,赴京赶考。一日路过一座寺庙,相师断言书生死期已近。书生将信将疑继续赶路。有一天,时近黄昏,他撞见一个孕妇手中抱着一个三岁婴儿,哭哭啼啼正欲跳河自尽。书生赶紧上前拉住,问其缘由。原来她家前日杀了一口猪,屠夫给了十块银元。晚上丈夫回家,一看十块银元是假的,结果夫妇俩为此相互埋怨,争吵不休。这妇人一时想不开,便偷偷跑出来欲寻短见。书生听后,便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银元悄悄替换,然后对那位妇人道:“是你丈夫胡说,这不是真的么?你拿回去叫你丈夫再仔细看看吧。”那妇人听罢,便半信半疑转回家去。结果可想而知,书生用十块银元更是用他的善心救下了该母子三条性命。
书生又行。一日,走累了,便在一堵断墙下坐下来歇脚。鬼使神差,刚坐下的他,又站了起来走开。就那一瞬间,那道墙“嘣”地一声塌了下来。好不惊险,差一点点,他就成了肉饼。
过了好些日子,这书生考中功名回转家来,途中又经过那个寺庙。他诘问那位相师:“你讲我死期已到,可我至今不是好端端的么?”那位相师答言:“这是因为你修得了阴功的缘故,非是我算得不准呀!”
父亲总是用古代仁善故事和自身言行倡导子女做人要诚信谦善,非礼勿做,非我莫取。早年他在安吉冶坊铸造、销售铁锅。有一日夜间,他歇宿盘账,发现钱款多出不少。他思前想后,料定是白天那位买锅的妇人花了眼,错把一百元当成了十元,而当时他接过钱后也未曾仔细察看。父亲决定第二天一早把钱送回去。可是他又想,也许此刻那户人家夫妇正在为此争吵呢。人命关天,弄不好还会出大事情。于是父亲摸黑而行,翻山越岭近二十里地,当夜把钱送还给了人家。
父亲一生养育七个子女,居家不易。他没有更多的钱财,但有的是力气。他勤劳吃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读。雨雪天气,农人难得休闲嬉戏,甚或搓麻将赌博,押宝取乐。可父亲不是!他要么进山砍竹、烧炭,挣钱养家。要么看书、抄写古籍、戏本。至今我的书柜里仍奉放着父亲遗我《论语集注》、《齐家要略》、《新增字类标韵》、《继善书》、《绘图粉妆楼》、《荡寇志》等木刻版线装书以及《姜维探营》、《花园得子》、《工尺谱》等手抄戏曲唱本。更多时候是父亲一个人,或带领我的哥哥姐姐去到石宕,肩挑背扛,取来块石、石渣修整路面。不光村庄周边,更带上饭食,去往一、二十里地以外的峰岘岭、杏桐园等古驿大道和山岭修路。所以周边百姓都知道我父亲是个善人,而且是个有些文化的善人。早年间,农村识字者不多,间或父亲会受托帮人写个对联、寿幛,或选个黄道吉日之类,一切义务帮忙。我自小喜欢涂涂画画,记得有一年遵父命,帮人画过一张钟馗驱鬼之类的瑞吉图。还有一次画的是一条金龙,据说是“祭度”之用。平日或逢年过节每有乞讨者上门,父亲从来和声细语,不让对方空手而去,并叮嘱我们善待乞者。记得我7岁光景,父亲带领哥姐嫂嫂,全家出动,义务投工,重修村中主要桥梁“大桥头”,由此带动村中一帮热心人士乃至过往行人一并参与。最终工程告竣,乡亲莫不欣然。这些年他最小的孙女似乎也承继了祖父急公好义的秉性,或山区支教,或当义工,或捐钱款。代有遗风,令我欣慰,此乃家门之幸。有付出便有收获,我想收获的并非一定非得是物质与财富,更重要的收获该是自己的心安、满足和一个健康的身心,兴许还有乡亲的认可与旁人的赞誉!
父亲待人以诚善,待子女以慈爱,待我尤甚。我是家中老小,年龄之故,我的影象里父亲从来就是一个慈祥的老者。唯一一帧我见过的父亲中年时的相片,也因故踪迹渺然,令我惋惜不已。更让我至今心有戚戚的是我曾经的少不更事。那时我尚在镇上念中学。每当降温的日子或是雨雪霏霏的周末,已年届古稀的父亲便会拄着拐杖,步行数里来到学校,为我添送衣服和一把半新不旧的油纸伞。父亲伫立于教室外边,临窗向里眺望。同学误以为是我爷爷,知道原委后不免耻笑。如此,我便有一种自卑,兼有一种小小的怨忖,但又不便与父明言。父亲自然也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他所以为的天经地义之举,而我的内心也便一再的纠结。风雨飘摇,回家的路上我顾自急急前行,不愿同父亲多说一句话。不多时候便同父亲拉开一段距离,唯余年迈的父亲在后边颤颤巍巍,紧追慢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家有慈父,雪中送暖,如今想来这是一副多么温馨,甚至让人热泪盈盈的画面呀。而年少的我,竟然不知珍惜,更心存怨尤,此种愧疚至今萦绕不去,永世难消!咦,上邪,时光能可倒流么?再不济,且容我梦回年少,重睹父容,忏悔自己曾经的冥顽无知!
父亲个头中上,身骨一向健朗。只是步入晚年之后,腿脚不便,步履蹣跚。尤其是话语不多,沈默如金。饭食渐减,面容逾益的瘦削,唯布满红红血丝的双眼慈光依旧。父亲是在83岁的时候过世的。时值春末,万物葱茏,春和景明。去世前了无征兆,无疾而终。民间说法,善有善报!灵异的是,走前的头夜,父亲竟赫然潜入我的梦境,想来该是同我道别。梦境里,我望见他身着长袍,循着老宅中的楼梯,缓步、安详地迈向高处,步往天国……从此天人永隔,不再回还!
2014年2月10日MU582航班飞行途中
END
撰写:应忠良(梦柯)
扫描二维码
关注更多“梦柯”
微信编辑人:我的名字叫红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